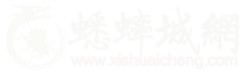(四)忆 斗
北京斗蛐蛐,白露开盆。早虫立秋脱殻(音‘俏’),至此已有一个月,可以小试其才了。在上局之前,总要经过‘排’。所谓‘排’,是从自己所有的蛐蛐中选份量相等的角斗,或和虫友的蛐蛐角斗。往往赢了一个还不算,再斗一个,乃至斗三个。因为只有排的狠,以后上局心中才有底,同时把一些不中用的淘汰掉。排蛐蛐不赌彩,但须用‘称儿’(即戥‘等’子),‘腰’份量,相等的才斗,以免小个的吃亏。自己排也应该如此。当然有的长相特别好的舍不得排,晚虫不宜早斗得也不排,到时候直接拿到局上去,名叫‘生端’。
称儿是一个长方形的匣子,两面插门。背面插门内镶有玻璃,便于两面看份量。象牙制成的戥子杆,正背面刻着分、厘、毫的标志,悬挂在匣子的顶板下。杆上挂着戥子铊。随着称儿有四个或六个‘舀子’,供几位来斗者同时使用。少了不够分配,蛐蛐约不完,耽误对局进行。
舀子作圆筒形,用竹筐内壁(竹黄)或极薄银叶圈成,有底有盖,三根丝线将筒和盖连接起来。线上端系金属小环,可挂在戥子的钩上,这是为装入蛐蛐称份量而制的。几个舀子重量必须相等,毫厘不差。细微的出入用黄蜡来校正,捻珠黏在三根丝线聚头处,籍以取得一致。
白露前几日,组织斗局者下帖邀请虫友届时光临,邮寄或事人送往。帖子内容如下:
兹定于八月十一日下午二时会斗秋虫敬请
光临 劲秋谨定
盆设朝阳门内南小街一七五号旁门
与一般请帖不同的是邀请者具名不写姓名,而写局上所报的‘字’。姓名可以在请帖的封套上出现。
蛐蛐局也有不同的等级。前秋的局乃是初级,天气尚暖,可在院子内进行,有一张八仙桌,几张小桌和椅子、凳子就行了。这样的局我也举办过好几年,用我所报的字‘劲秋’具名邀请。院子是向巷口已开张的赵家灰铺租的,每星期日斗一次。局虽简陋,规矩却不能错,要有五六个人就能唱好这台‘戏’。
一个司称,需提前到局,以便将舀子的份量校正好。校正完毕,坐在称儿前,等待斗家将虫装入舀子送来称重量。
一个司帐,画好表格,记录这一局的战况。表格有个固定格式,已沿用多年,设计合理,简明周密,一目了然。(这里不列明细样张)
司帐者桌上摆着笔墨、纸张、裁纸刀等,兼管写条子。条子用白纸或色纸裁成,约两寸宽,半尺长,盖上司帐者印章,以防有人作弊,更换条子。斗家到局,先领舀子,装好蛐蛐,送去过秤。称好一虫,司称高唱某字重量多少。司帐在表格的第二格内写报字,第三格内用苏州码子写蛐蛐的份量。另外在一张条子上写报字和份量,交虫主持去,压在该虫的罐子下。另外在一张条子上写报字和份量,交虫主持去,压在该虫的罐子下。各家的蛐蛐登记完毕,就知道今天来了那几家,各有多少条虫,各虫份量多少。斗家彼此看压在罐下的条子,就知道自己的蛐蛐和谁家的份量相等,可以栓对。司帐根据表格也会不时的提醒大家,谁和谁‘有对’。
一人监局,站在八仙桌前,桌上铺红毡子,旁放毛笔一枝,墨盒一个。桌子中央设宽大而底又不甚光滑的瓦罐,名为‘斗盆’。两家如同意对局,各把罐子捧到斗盆一侧。监局将两张条子并列摆在桌上。这时双方将罐盖打开,进行‘比相’。因为即使份量相等,如一条头大项阔,一条头小项窄,项小的主人会感到吃亏而不斗。比相后同意对局,再议赌彩。早秋不过赌月饼一两斤。每斤月饼折钱多少,由司帐宣布,一般为五角或一元。议定后,监局将月饼斤数写在两家的条子中间,有如骑缝,字迹各有其半。
双方将蛐蛐放入斗盆,各自只许用黏有鼠须得芡子撩逗自己的蛐蛐,使之有敌来犯。当两虫牙钳相接,监局须立即报出‘搭牙’,算是战斗已经打响,从此有胜有负,各无反悔。不论交锋的时间长短,回合多少,上风下风有无反复,最后以‘一头一面’判输赢。所谓‘一头’、‘一面’乃是一回事,即下风蛐蛐遇见上风,贴着盆腔掉头逃走。如此两次,便是输了。倘向盆腔相反方向掉头逃走,名曰‘外转’;向前逃窜,名曰‘冲’,都不算‘头’或‘面’。不过监局也须大声报出,好让虫主和观众都知道。监局实负有裁判员的职责。胜负即分,监局在胜者的条子上写个‘上’字,在负者的条子上写个‘下’字。两张条子一并交到司帐那里。司帐根据条子在表格上胜者一栏的第一格里写蛐蛐的重量及所赢月饼的斤数,在负者一栏的第四格里写蛐蛐的重量及所输的月饼斤数。两张条子折好存在司帐处,趟有人要复查,此是凭证。各家结账时据第一、第四两格的输赢数字,结算盈亏。
上述三人是局上的主要人员,此外还须一两人沏茶灌水,照料一切。一局下来,他们分抽头二成所得,每人可得几块钱。
倒不是我夸口,三十年代由我邀请的初级小局,玩得比较高尚文雅。来者岁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但很少发生争执或有不局气的行为。赌彩既微,大家都不在乎。不少输了钱如数缴纳,赢了却分文不要,留给局上几位忙了一天的先生们一分了事。这当然和早秋季节有关,此时大小养家蛐蛐正多,心爱之虫尚未露面,骁勇之将或以亮相,但尚未立多少战功,所以上局带有练兵性质,谁也不想多下赌注。
中秋以后,天凉多风,院里已不宜设局。这时自有大养家出面邀请到家中对阵,蛐蛐局也就升了级。善战之虫已从几次交锋中杀了出来,渐有名声。赌彩倘仍是一两斤月饼,主人会感到和虫的身价太不相称了。
只要赌彩大了,事情也就多了,不同人物的品格性情也就一一表现出来。有的对上称约份量十分计较,老怕司称偏心他人,以致吃了亏。他在称的背面盯着戥子,嘴里唠叨着:“不行吧,拉了一点吧,您再往里挪挪。”所争的可能还不到一毛(即一毫)的重量。甚至有人作弊,把舀子上的蜡珠偷偷扣下一点。自己占了便宜却弄得舀子的份量不一致。被人发现,要求对所有的舀子都复查核对,把局吵了,弄得不欢而散。
斗前比相,更是争吵不休,总是各自贬低自己蛐蛐的长相,说什么:“我的头扁了,脖子细了,肚子大了,比您的差多了,不是对!不是对!”实则未必如此。有的人心中有一定之规,那就是,相上如占不到便宜,就是不斗。
在观众中,随彩的也多了。有的只是因为和虫主有交情,随彩为他助威。有的则因某虫战功赫赫,肯定能赢,故竞相在它身上压赌注。倘对局双方均是名将,各有人随彩,那热闹了。譬如‘义'字和‘山’字对阵,双方已议定赌彩,忽一边有人喊道:“‘义’字那边写‘爽秋两块’。”又有人喊:“天字两块。”对面有人应声说:“山字那边写叨字两块。”跟着有人喊:“作字随两块。”这时忙坏了监局,他必须在两边条子上把随彩人的报字和所随的钱数一一记上,分胜负后司帐好把随彩移到表格上。随彩者如没有蛐蛐,他的报字也可以上表格,只是第三格中不会有蛐蛐的分量而已。有时斗者的某一方不常上局,显得陌生,他就难免受窘,感到尴尬。因为观阵者都向对方下注,一下子就增加到几十元。如果斗,须把全部赌注包下来,未免输赢太大。不斗吧,又显得过于示弱,深感进退两难。
使芡子是一种高超的技艺。除非虫主是这方面的高手,总要请专家代为掌芡。运用这几根老鼠须子有很大的学问。但主要是当自己的蛐蛐占上风时,要用芡子激发神威,引导它直捣黄龙,使对方一败涂地。而处于下风时,要用芡子遮挡封护,严防受到冲击,好让它得到喘息,增强信心,恢复斗志,以期达到反败为胜的目的。但双方都不能做的过份,以致触犯定规,引起公愤。精彩的对局,不仅看斗虫,也看人斗。欣赏高手运芡之妙,也是一种艺术享受。那怪自古即被人重视,《蚟孙鉴》有专条记载运芡名家姓氏,传于后世。
清末民初,斗局准许用棒,在恩溥臣《斗蟋随笔》中有所反映,而为南方所无。对阵时,占上风上一方用装芡子的硬木棒轻轻敲打盆腔,犹如擂鼓,为虫助威。这对下风当然大大不利。三十年代已渐被淘汰,偶见使用,是经过双方同意的。
监局即是裁判,难免碍于人情或受贿赠而偏袒一方。这在将分胜负的时容易流露出来。他会对一方下风的‘一头一面’脱口而出,甚至不是真正的掉头败走也被报成‘头’、‘面’。而对另一方下风时,‘一头一面’竟支吾起来,迟迟不报。执法态度悬殊,其中必有不可告人处。
局上可以看到人品性格,众生相纷呈毕现。有人赢了,谦虚地说声:“侥幸。”有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向对方投以轻蔑的眼光。输了,有人心悦诚服,自认功夫不到家,一笑置之,若无其事。有人则垂头丧气,默默不语,一虫之败,何至懊丧如此?!更有面红耳赤,怒不可遏,找碴强调客观原因,不是说比相吃了亏,就是使火没使够。甚至埋怨对方,为什么催我上阵,以致没有过铃子,都是你不好,因此只能认半局,赌彩只输了一半。
上面讲到的局,一般有几十元的输赢,还不能算真正的蛐蛐赌局。真正的赌局斗一对下注成千上万,这只有天津、上海才有。据说在高台上斗,由一人掌芡,只许双方虫主在旁,他人无从得见。这样的局不要说去斗,我一次还没有参观过呢。即使有机会参观,我也不会去!
北京过去最隆重的蛐蛐局要数‘打将军’,多在冬至前或冬至日举行,它带有年终冠军赛和一季秋虫活动圆满结束的双重意义。襄生也晚,没有赶上本世纪初麻花胡同纪家、前马场钟杨家、那王府、杨广字、余叔岩等大养家的盛期。当时几乎每年都打将军,《斗蟋随笔》就有记录。
打将军或在家中,或在饭庄,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曾承办多次。老友李桐华(‘山’字)曾告诉我盛会的情况:邀请之家事先发请帖,届期各养家到会,把式们用圆笼挑着蛐蛐罐及汤壶前来。虫贩只限于资格较深并经主人烦请帮忙者始得与会。中堂设供桌,先举行请神仪式。上方正中安神位,供的是蚂蚱神。桌上摆香炉蜡烛,五堂供,三堂面食,两堂果子。先由主人上香行礼,继之以各位养家,长者在前,依齿而行,叩头或揖拜听便。此后虫佣虫贩顶礼,必须跪拜磕头。请神完毕,对局开始,过秤、记账、监局等一如常局。惟斗后增加卖牌子活动。牌子由司称、司帐等准备,红纸上书‘东征大将军’、‘征西大将军’、‘征南大将军’、‘征北大将军’、‘九转大虫王’、‘五路都虫王’等封号。胜者受到大家的祝贺,自然高高兴兴去买牌子。牌子两元、四元、六元、八元不等,买者买个喜气,图个吉祥,而带有赏赐性质,局上各位忙了一季,这是最后一笔收入。打完将军,虫王、将军陈至供桌上,行送神礼,虫佣虫贩需再次叩头。礼毕将宝盖、幡、七星纛(音‘道’)送至门外,在音乐声中火烧焚化。送神后入宴席,养家和佣贩分开落座。前者为鸭翅席,后者为九大件。宴席后大家拱手告别,齐到明秋再见。
打将军封建迷信色彩浓厚,而且等级分明,它也不是以赌博为目的,而是佣贩帮闲伺候王公大人、绅士富商游玩取乐的活动。一次打将军主办者不惜一掷千金,要的是派头和‘分儿’,这种耗财买脸的举动,六七十年来久已成为陈迹了。
(五) 忆 器
南宋时,江南养蟋蟀已很盛行。一九六六年五月,镇江官圹桥发现古墓,出土三具过笼。报道称:“都是灰陶胎,两只为腰长形,长七厘米,两头有洞,上有盖,盖上有小纽,纽四周饰六角形双线网纹。其中一只内测有铭文四字,残一字,‘X名朱家’。另一只为长方形,长亦七厘米,作盖顶式,顶中有一槽,槽两侧饰圆珠纹。圆珠纹外边斜面上饰料方如意纹,一头有洞。长方形的蟋蟀过笼,一头有洞,当是捕捉蟋蟀时用的。腰长形过笼两头有洞,宜于放置圆形斗盆中放蟋蟀用的。”(见《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五期封三)
所谓腰长形的即外壁一边为弧形,可以贴着盆腔摆放。一边外壁是直的,靠着它可以放水槽。这是养盆中的用具,报道谓用于斗盆,实误。仅一端有洞的因不能穿行,已不得称之为过笼。北京有此用具,名曰‘提舀’。竹制,上按立柄,用以提取罐中的蛐蛐。捉蟋蟀是用不上的。古墓年代约为十二世纪中叶,所以三具为现知最早的蟋蟀用具。可证明约一千年前它已定型,和现在仍在使用的没有什么区别。
宋代蟋蟀盆只见图像,未见实物。万历间刊行的《鼎新图像虫经》绘盆四具。其中的宣和盆、平章盆可理解为宋器,至于标名为王府盆、象窑盆,时代就难说了。四盆并经李大翀(音‘充’)《蟋蟀盆》摹绘,造型、花纹与《虫经》已大有出入。当因摹者随手描绘所致。故类此图像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材料,而无法知道其真实面貌。李谱还有所谓‘宋内府镶嵌八宝盆’、‘元至德盆’、‘永乐盆’,未言所据,来源不明。这些图的价值,比该书《盆考》述及的各盆也高不了多少,它们的可靠性要待发现实物才知道,现在只能姑妄听之而已。本人认为谈蛐蛐罐不能离开实物,否则终有虚无缥缈之感。本文所及品色不多,去详尽尚远,但都是我曾藏或曾见之物。不尚空谈,当蒙读者许可。
养家都知,蟋蟀盆有南北之分,其主要区别在南盆腔壁薄而北盆腔壁厚,这是南暖北寒地气候决定的。我所见的最早实物为明宣德时所制,乃腔壁较厚有高浮雕花纹的北式盆。这是因为自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公元一四二一年)国都北迁后,宣宗朱瞻基养蟋蟀已在北京的原故。罐高十一厘米,径十四点五厘米,桐华先生旧藏,现在天津黄绍斌先生处。盖面中心雕两狮想向,爪护绣球,球上阴刻万胜锦纹,颇似明雕漆器上所见。左右飘丝绦。空隙处雕花叶。中心外一周匝浮雕六出花纹,即常见于古建筑门窗者。在高起的盖边雕香草纹。罐腔上下有花边两道,中部一面雕太狮少狮,俯仰嬉戏,侧有绣球,绦带飞扬。对面亦雕狮纹,姿态略有变化。此外满布花卉山石。罐底光素,中心长方双线外框,中为阳文‘大明宣德年造’六字楷书款,于宣德青花瓷器、剔红漆器上所见,笔意全同。故可信为宣德御物。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龙纹罐,盖内篆纹戳记‘仿宋贾氏珍玩醉茗痴人秘制’十二字,罐底龙纹图记内有‘大明宣德年制’款(见石志廉《蟋蟀罐中的几件珍品》,《燕都》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曾目见,戳记文字及年款式样均非明初所能有,乃妄人伪造。
我因久居北京,对南方盆罐一无所知。北方名盆,高中读书时开始购求,迨肄业研究院,因不再养蛐蛐而终止,前后不足十年,有关知识见闻,于几位秋虫老宿相比,自然相去远甚。
秋虫老宿,近年蒙告知盆罐知识者有李桐华、黄振风两先生。桐华先生谢世已数载,振风先生则健在,惟十年浩劫,所藏名盆已多成瓦砾矣。
北京盆罐为养家所重者有两类,亦可称之为两大系列,即‘万里张’于‘赵子玉’。万里张咸知制于明代,底平无足,即所谓‘刀切底’。盖内有款识,盖、罐骑缝有戳记。戳记或为笔管,或为‘同’字,或近似‘菊’字而难确认。澄泥比赵子玉略粗,故质地坚密不及,术语称之曰‘糠’。正因其糠,用作养盆,实胜过子玉,其带皮子有包浆亮者尤佳。同为万里张,盖内款识不同,至少有八种,再加净面无纹者则就有九种,此非深于此道者不能言。桐华先生爱万里张胜于子玉,故知之独详。我历年收得四种,再加桐华先生所藏,尽得寓目,并拍摄照片,墨拓款识,故大体齐备。以下为明万里张各盆款记:明万里张盖内款‘万里张造’(盆直径13厘米)、明白山(万里张)罐底款(盆直径11.9厘米)、永战三秋(万里张)罐底款(盆直径12.2厘米)、永站三秋(万里张)罐底款(盆直径12.9厘米)、怡情雅玩(万里张)罐底款(盆直径12.6厘米)、春游秋乐(万里张)罐底款(盆直径11.9厘米)。
赵子玉罐素有十三种之说。邓文如师《骨董琐记》卷六记石虎胡同蒙藏学校内掘出蟋蟀盆,属于赵子玉系统者有:淡园主人、恭信主人之盆、古燕赵子玉造、敬齋主人之盆、韻亭主人之盆等五种,不及十三种之半。清末拙园老人《虫鱼雅集》《选盆》一条所记十三种为:白泥、紫泥、藕合盆、倭瓜瓤、泥金罐、瓜皮绿、鳝鱼青、黑花、淡园、大小恭信、全福永胜、乐在其中。《雅集》所述相虫、养虫经验多于虫佣、虫贩吻合,此说似亦为彼等所乐道。桐华先生以为其不能令人信服处在前九种即以不同颜色定品种,何以最后又将四种不同款识之盆附人。一似列举颜色难足其数,不得不另加四种,凑满十三。故子玉十三种应以不同款识者为限,分列如下:一、‘古燕赵子玉造’,桐华先生特别指出此六字款如末一字为‘制’而非‘造’,皆伪,屡验不爽。‘都人子玉’则真者末一字为‘制’而非‘造’;二、淡园主人;三、都人赵子玉制;四、恭信主人盆(大恭信);五、恭信主人之盆(小恭信);六、敬齋主人之盆(大敬齋)二号盆;七、敬齋主人之盆(小敬齋)三号盆;八、韻亭主人盆;九、闲齋清玩;十、大清康熙年制;十一、乐在其中;十二、全福永胜;十三、净面赵子玉,光素无款识。
黄振风先生则别有说,认为赵子玉不仅有十三种,且另外还有‘定制八种’,亦即赵子臣所谓‘特制八种’,而‘大清康熙年制’因非子玉所造,故不与焉。‘八种’并经振风编成口诀,以便记忆:全福永胜战三秋,淡园韻亭自古留,敬闲二齋双恭信,乐在其中第一流。‘八种’之戳记分别印在盖背面及足内。其款识及戳记外框形式如左:一、‘全福永胜’,盖背面横长圆外框,一名‘枕头戳’,四字自右而左平列。足内长方形外框,‘古燕赵子玉造’,两行,行三字。二、‘永战三秋’,四瓣柿蒂式外框,每瓣一字,‘永’在上,‘战’在右,‘三’在左,‘秋’在下。三、‘淡园主人’,方形外框,两行,行两字。四、‘韻亭主人盆赵子玉制’,大方形外框,三行,行三字。五、‘敬齋主人之盆’,窄长方形外框,天津称之曰‘韮菜扁戳’,一行六字。六、‘闲齋清玩’,方形外框,两行,行二字。七、‘恭信主人盆赵子玉制’,大方形外框,三行,行三字。此为‘大恭信’。‘恭信主人之盆’,窄长方形外框,一行六字。此为‘小恭信’。大小恭信以一种计。八、‘乐在其中’,盖背面方形外框,两行,行二字。足底内‘都人赵子玉制’,长方形外框,两行,行三字。此罐比以上七种更为名贵,故曰‘第一流’。
以上惟‘淡园主人’及‘小恭信’为三号罐,余均为二号罐。又唯有‘敬齋’及‘乐在其中’两种足底外缘做出凹入之委角线,名曰‘退线’,余六种无之。
振风先生背诵子玉十三种之口诀为:瓜皮豆绿倭瓜瓤,桃花冻红鳝青黄,黑白耦合泥金盆,净面都人足深长。‘十三种’中净面光素无款识。都人子玉款识为‘都人赵子玉制’,长方形外框,两行,行三字。其余十一种款式均为‘古燕赵子玉造’,长方形外框,两行,行三字。振风同意桐华先生之说,‘古燕赵子玉造’款式凡末字为‘制’而非‘造’者,皆伪。并指出‘古’字一横下,或有一丝两端下弯之线,或无之,二者皆真。有弯线者乃戳记使用即久,出现裂纹之故。据此推测,戳记当用水牛角刻成。
一、瓜皮绿;二、豆瓣绿;三、倭瓜瓤,其色易于鳝鱼黄混淆,分别在倭瓜瓤盖面平坦,而鳝鱼黄盖面微微隆起,亦曰‘馒头顶’;四、桃花冻,其色红于藕合盆;五、鳝鱼青;六、鳝鱼黄;七、黑花;八、白泥;九、藕合盆,其色接近浅紫,十三中惟此底足有退线;十、泥金盆,罐上有大金星及金片,如潵金笺纸;十一、净面;十二、都人赵子玉制,盖与足底款识相同,凡末字作‘造’而非‘制’者皆伪;十三、深足子玉,罐底陷入足内较深。
黄振风先生与拙园老人之说,可谓大同小异,故似出同源。其所以被称为‘十三种’,除确知为赵子玉所造外,皆无定制者款识,于‘定制八种’之区别即在此。黄先生既能言之甚详,且谓‘八种’、‘十三种’曾与赵子臣商榷印证,可谓全同。不言而喻,桐华先生之说与子臣大不相同。
桐华、振风两先生之虫具知识,笔者均甚心折,而子臣既出虫贩世家,更一生经营虫具,见多识广,又非养虫家所能及,故其经验阅历,尤为值得重视。笔者自愧养虫资历不深,名罐所藏有限,且有未经寓目者,因而不能判断以上诸说究以何为可信,只有一一录而存之,以备进一步之探索及高明博雅之指教。惟究其始,赵子玉当年造盆,不可能先定品种‘八’与‘十三’之数,并以此为准,不复增减,其理易明。后人据传世所有,代为落列排比,始创‘八种’、‘十三种’之说,此殆(音‘带)事物之规律。若然,则各家自不妨据一己之见而各有其说。各说亦自可并存而不必强求其一致矣。
赵子玉罐虽名色纷繁,然简而言之,又有共同之特征,即澄泥极细,表面润滑如处子肌肤,有包浆亮,向日映之,仿佛呈绸缎之光而绝无由杂质之反射,出现织细之闪光小点。棱角挺拔,制作精工,盖腔相扣,严丝合缝,行家勿庸过目,手指抚摸已知其真伪。仿制者代有其人,甚至有在古字一横下加弯者,矜持拘谨,不难分辨。民国时大关虽竭力追摹,外形差似而泥质远逊。
万里张及赵子玉均有特小盆罐,或称之为‘五号’,超出常规,遂成珍异。某家有一对,何人藏四具,屈指可数,为养家所乐道。实物如桐华先生之小万里张,四具一堂,装入提匣,专供前秋、中秋上局使用。小子玉则有邓西忠旧藏一对‘乐在其中’,直径不到十厘米盖背面款识为‘乐在其中’足底内为‘都人赵子玉制’堪称绝品。可能为王府公主或内眷定制者。填土虽贱,却珍逾球璧。
其他名罐如‘瓦中玉土精盆’,雕镂蝴蝶而填以色泥,故又曰‘蝴蝶盆’。‘南楼雅玩’盆,主人即《虫鱼雅集》述及曾养名虫‘蜈蚣紫’,咬遍京华无敌手,死后葬于园中纡环轩土山上,并为建虫王庙之南楼老人。此盆并非用澄泥轮旋成形,而是取御用金砖斧砍刀削,砥砺打磨而成。四字款识亦非木戳按印而是刃凿剔刻出阳文文字。所耗人力物力,超过泥填窑烧,何止千倍!其他私家制罐,款识繁多,道光时‘含方园制’盆乃其佼佼者。用泥之细不亚于子玉,款识亦朴雅可喜。
一般养盆以有赵子玉为款者为多,戳记文字式样,不胜枚举。其他款识也难讲述,大小造型,状态不一,因不甚被人重视,故更缺乏记载可稽。
过笼,北京又称‘串儿’,谓蛐蛐可经两孔串来串去。名贵的过笼同样分万里张、赵子玉两个系列。
万里张过笼轮廓柔和,造型矮扁,花纹不甚精细,不打戳记而代之以在盖背面按印指纹。下举二例:一、万里张菊花纽(亦有称葵花纽)过笼,除纽外全身光素,有大小两种。二、万里张五福捧寿过笼,纽为高起的圆寿字,四周五福围簇。
赵子玉过笼棱角快利,立墙较高,花纹精细,不加款识。常见盖内印有叶形戳记中有赵子玉三字者皆是赝品。下举真者数例:一、赵子玉单枣花、双枣花过笼,亦有称之为桂花者,除纽外全部光素。造型大小有别,小者又名‘方寸’,宜用于晚秋较小的盆中。又有扇面式的,月牙形水槽贴着摆放,可为盆内留出较大空间。二、赵子玉五福捧寿过笼,与万里张相似而花纹较繁,将光纹改为纹地。于此亦可见前后的渊源关系。如过笼正面立墙有刀割花纹,则名曰‘五福捧寿拉花’。‘拉’北京方言刀刻之意。三、赵子玉鹦鹉寿桃过笼,寿桃作纽,两侧各有展翅鹦鹉。亦名‘鹦鹉偷桃’。如立墙有刀刻花纹,名为‘鹦鹉寿桃拉花’。
所谓旧串,和旧养盆一样,花色繁多。其佳者为‘含芳园制’。盖上印有菊蝶、古老钱、蟠龙、花卉等花纹者以及红泥、黑花等又逊一筹。
《虫鱼雅集》讲到:“水槽亦有真伪。至高者曰蓝宝文鱼,有沙底,有瓷底。次则梅峰、怡情、宜春、太极、蜘蛛槽、螃蟹槽、春茂轩,不能尽述。”怡情朱色勾莲于嘉、道时。春茂轩各式乃太监小德张为慈禧定烧,出光绪景德镇窑。昔年笔者一应俱全,且有德化白瓷、宜兴紫砂以及碧玉、白玉、玛瑙者。十年浩劫,散失殆尽矣。
上局用具还有净水瓶,即大口的玻璃瓶。或用清代舶来品盛洋烟的‘十三太保’瓶,因每匣装十三瓶而得名。磨光玻璃有金色花纹,十分绚丽。其用途是内盛净水及水藻一茎。蛐蛐胜后,倾水略刷其盆,掐水藻一小段放盆内,供其滋润牙帘。
此外还有放在每一个罐上的‘水牌’。扁方形,抹去左右上角。考究的为象牙制,次为骨或瓷。正面写虫名、买的日期、产地及重量。背面为每次战斗记录、包括日期、重量、战胜某字某虫等。它分明是为蛐蛐建立的档案。北京的规矩,非经同意不得翻看别人的水牌。
其他用具如竹夹子、蔴刷子、竹制食抹等均为消耗品,从略。惟深秋搭晒所用竹簾,分粗细三等。极细者真如蝦须,制作极精,今亦成为文物亦。
(六) 忆 友
七十年来由于养蛐蛐而认识的人实在太多了,结交成契友的也不少,而最令人怀念的是曾向我传授虫经的几位老先生。
赵李卿,武进人,久居北京。北洋政府时期,任职外交部,是我父亲的老同事,看我长大的。在父执中,我最喜欢赵老伯,因为他爱蛐蛐,并乐于教我如何识别好坏。每因养蛐蛐,受到父母责备,我会说:“连赵老伯都养。”好像理由很充足。他也会替我讲情,说出一些养蛐蛐有好处的歪理来。我和他家相距不远,因此几乎每天都去,尤其是到了秋天。
赵老伯上局报‘李’字,所有卖蛐蛐的都称他‘赵李子’。长腿王喜欢学他带有南方口音的北京话,同时举手用食拇两指相聚寸许地比划着:“有没有大黄蛐蛐?”他确实爱黄蛐蛐。因为养过特别厉害的,对黄蛐蛐也特别有研究,能说出多种多样的‘黄’来---哪几种不中用,哪几种能打到中秋,哪几种才是常胜将军。他想尽方法为我讲解,并拿颜色近似的蛐蛐评比差异。但最后还是说只有遇到标准虫才能一目了然,还要养过才记得住。这就难了,谈何容易能碰到一条。有一年还真是碰到了。陆鸿禧从马坊逮回来的头如樱桃而脑线闪金光的紫黄蛐蛐。他认为是黄而非紫。因是早秋,他说要看变不变。如变深了就成紫蛐蛐了,也就不一定能打到底了。如不变深,则是虫王。他的话灵验了,金黄色始终未退,连赢八九盆,包括‘力’字吴彩霞的红牙青。而‘力’字是以特别难斗著名的。每次对阵紫黄都是搭牙向后一勒,来虫六足蹬着罐底用力才挣扎出来。一口净,有的尚能逃窜,有的连行动都不灵了。赵老伯看其他颜色蛐蛐也有经验,但自以为对黄的最有心得。我最早相虫,就他领进门的。
赵伯母是我母亲的好友,也很喜欢我。她最会做吃的,见我去总要塞些吃的给我。至今我还记得她对赵老伯说的一句话:“我要死就死在秋天,那时有蛐蛐,你不至于太难过。”二老相敬如宾,真是老而弥笃。
白老先生住在朝阳门内北小街路东,家设私塾,教二三十个启蒙学生。高高身材,微有髭须。出门老穿袍子马褂,整齐严肃,而就是爱玩蛐蛐。上局他报‘克秋’,故人称白克秋,名字反不为人知。
不认识他的人,和他斗蛐蛐,容易栓对。因为他的虫都是小相,一比对方就会欣然同意。但斗上才知道,真厉害!他的蛐蛐通常一两口就赢了。遇上硬对,又特别能‘驮口’,咬死也不走,最后还是他赢。我还不记得他曾输过。养家经过几次领教,有了戒心,都躲着他。即使在相上明显占便宜也不敢贸然和他交锋。
我几次看他买蛐蛐,不予人争,总是等人挑完了才去看。尤其是到了蛐蛐店,明言:“‘拿下水’给我挑。”每次不多买,只选两三条。价钱自然便宜不少,因为已被人选过多次了。不过往往真厉害的蛐蛐并未被人挑走而终为他所得。真是千里马虽少而伯乐更难逢。
我曾向白老求教,请示挑蛐蛐的标准。他说:“为了少花钱,我不买大相的,因为小相的照样出将军,主要是立身必须厚。你的大相横着看有,我的小相竖着有,岂不是一样?立身厚脸就长,脸长牙就长,大相就不如小相了。”记得他有一条两头尖的蛐蛐名曰‘枣核丁’,是上谱的虫,矫健如风,口快而狠,骁勇无比。每斗一盆,总把对方咬得满罐子流汤。如凭长相,我绝对不会要它。白老选虫还有许多诀窍,如辨色、辨肉等,也曾给我讲过,但不及立身厚那样容易领会理解。
白老每年只养二三十条蛐蛐,因此上局从不多带,少则两条,多则四条。天冷时,只见他白布手巾把一对瓦罐摞起一包,提着就来了。打开一看,两罐中间夹着一块热饼。一路行来,使火恰到好处。蛐蛐过了铃子,他饼也吃完了。他总是花最少的钱,用最简单的办法,取得最好的效果。
宣武门外西单草场内山西街陶家,昆仲三人,人称陶七爷、陶八爷、陶九爷,都以养蛐蛐闻名。尤以七爷陶仲良,相虫、养虫有独到之处。当年蛐蛐局有两句口头语:“前秋不斗山、爽、义。后秋不斗叨、力。”‘山’为李桐华,‘爽’为赵爽秋,‘义’为胡子贞,‘力’为名伶吴彩霞,‘叨’即陶仲良。意谓这几家的蛐蛐特别厉害,以不斗为是。而后秋称雄,更体现了养的功夫。
我的堂兄世中,是陶八爷之婿,故有姻戚之谊。不过我们的交往,完全由于同有秋虫之癖。
陶家是大养家。山西街离蛐蛐店很近,常有人送虫来。九爷家住济南,每年都往北京送山蛐蛐。他们最多养到十几桌,将近三百头。当我登门求教时,仲良年事已高,不愿多养,但蛐蛐房还是占用了三间北屋。
时届晚秋,‘叨’字拿出来的蛐蛐宝光照人,仍如壮年。 肚子不空不拖,恰到好处。爪锋不缺,掌心不翻,按时过铃,精神旺盛。下到盆中,不必交战,气势上已压倒了对方,这是精心调理之功。他的手法,主要利用太阳能,簾子遮挡,爆日取暖,簾子分粗、中、细三等,籍以控制温度,而夜晚及阴晦之日则用汤壶。前《忆养》讲到的‘搭晒’,就是他传授的方法。不过其不可及处在对个别蛐蛐采用不同的调理方法,并非完全一致。常规中又有变化,此又非我所能知矣。至于对爪锋及足掌的保护,他认为和罐底有极大关系。底太粗会挂断爪锋,太细又因打滑而致翻掌。因此后秋所用罐,均经严格挑选,一律用原来旧底而粗细又适度的万里张。陶家当年藏罐之多也是罕有其匹的。
李凤山,生于一九零零年,卒于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字桐华,以字行,蛐蛐局报名‘山’字。世传中医眼科,善用金针拔治痧眼、白内障等,以‘金针李’闻名于世,在前门外西河沿一九一号居住数十年。
桐华七岁开始捉蛐蛐,年二十七,经荣茂卿介绍去其兄处买蛐蛐罐。其兄乃著名养家,报字‘南帅’,选虫最有眼力。因患下痿,不能行动,故愿出让虫具。桐华有心向南帅求教,买罐故优其值,并为延医诊治,且常往探望,每往必备礼物四式,如是经年,南帅妾进言曰:“何不教教小李先生?”半晌,南帅问桐华:“你认识蛐蛐吗?”桐华不语。南帅说:“你拿两把来看看。”桐华从家中选佳者至。南帅命桐华先选一头。桐华以大头相重逾一分者进。南帅从中取出约八九厘者,入盆交锋,大者败北。如是者三,桐华先选者均不敌南帅后选者,不觉耳红面赤,汗涔涔下,羞愧难当。南帅笑曰:“你选的都是卖钱的虫,不是打架的虫。”桐华心悦诚服,自此常诣南帅处聆听选虫学,两年后,眼力大进。
桐华一生无他好,唯爱蛐蛐入骨髓。年逾八旬,手捧盆罐,尤欢喜如顽童,此亦其养生之道,得享大年。当年军阀求名医,常迎桐华赴外省,三月一期,致银三千元。至秋日,桐华必谢却赠金,辞归养蛐蛐。爱既专一,严钻遂深。中年以后,选、养、斗已无所不精,运芡更堪称首屈一指。有关虫事,每被人传为佳话。如虫友自天津败归,负债累累。借桐华虫再往,大获全胜,赢得赌注,数倍于所失。余叔岩摆蛐蛐擂台,久无敌手,桐华一战而胜,叔岩竟老羞成怒,拂袖而去。经人说项,始重归于好。李植、赵星两君已写入《京都蟋蟀故事》(共八篇,连载于一九九零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二月二日《中国体育报·星期刊》),今不再重复。唯对桐华平生最得意之虫,尚未述及,不可不记。易州人尚秃子从山东长清归来,挑中有异色小虫,淡于浅紫,蛐蛐从来无此色,无以名之,称之为‘粉蛐蛐’。多次赴局,重量仅六厘六,交牙即胜,不二口。是年在麻花胡同纪家打将军,杨广字重赏虫佣刘海亭、二群,以上佳赵子玉盆四具,从天津易归常胜将军大头青,以为今年‘五路都虫王’,非我莫属。大头青重八厘四,桐华自知所携之虫,无份量相等者。不料过后称,粉蛐蛐竟猛增至八厘四。与大头青对局,彼果不弱,能受两三口,但旋即败走。‘广’字大为懊丧。行送神礼,虫王照例放在供桌上。二群三叩,粉蛐蛐竟叫三声,于叩首相应,闻着莫不咄咄称奇。尤其者,次日在家再过秤,又减轻至六厘六。昨之八厘四似专为与大头青对局而增长者。后粉蛐蛐老死,六足稳立罐中,威仪一如生时。凡上种切,桐华均以为不可思议,不禁谓然曰:“甚矣哉蛐蛐之足以使人神魂颠倒也!”
我和桐华相识于一九三二年,他惠临我邀请的小局。次年十月,在大方家胡同夜局,我出宝邸产重达一分之黑色虎头大翅与桐华麻头重紫交锋,不料闻名遐迩‘前秋不斗’之‘山’字竟被中学生之虫咬败,一时议者纷纷。十一月,桐华特选宁阳产白牙青与虎头大翅再度对局,大翅不敌,桐华始觉挽回颜面。‘不打不相识’,二人自此订交。此后时受教益,并蒙惠赠小恭信盆及万里张过笼等。先生有敬齋盆二十有三,恰好我有一具,即以奉贻,凑成一桌,先生大悦,常向人道及我赠盆事。
一九三九年后,我就读研究院,不复养虫,直至桐华谢世,四十余年间,只要身未离京,秋日必前往请侯,并观赏所得之虫,先生常笑曰:“你又过瘾来了。”一九八二年后,曾念及何不请先生口述,试为总结选虫、养虫及鉴别虫具经验。惟此时正忙于编写有关家具、装饰诸作,邀请讲授只两三次,所获已写入本篇,未能作有系统之记录。今日思之,深感怅惘。
编辑《蟋蟀谱集成》,再使我怀念桐华先生。他如果健在,《集成》一定可以编得更好一些,《六忆》也可以写得更充实一些,生动一些。
后 记
我早年买到几种蟋蟀谱,均为常见本。后来去图书馆查资料,总要附带看一看所藏的蟋蟀谱。惟知有明刊本传世是在一九八七年黄裳兄发表《中秋随笔》之后,并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查到其藏所的。承顾起潜前辈热心介绍,蒙天一阁文物保管所允许拍摄书影,上海图书馆慷慨提供缩微胶卷,黄裳兄又赠我十分罕见的《功虫录》,这才使我产生为编一部丛书的想法。在进一步的搜集中,又得到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支持,所得逐渐趋完善。今离尚有待访之书,可能已不多了。总之,本书之得以辑成,是各图书馆及师友们大力支援的结果。而辑成之后,得以列入上海文化出版社影印计划,则端赖蔡耕先生推荐之功。期间联系拍照,编排制版,亦倍感辛劳。以上都是我衷心铭感而不敢或忘的。
在附录《秋虫六忆》中有不少虫具的拓片和照片。原器多为老友李桐华先生所藏。惟宣德狮纹盆是在天津黄绍斌先生入藏之后才拍摄到的。墨拓乃出名家傅大卣(音‘有’)先生之手。摄影由张平、罗阳两位同志任其事。今一并在此致谢。各谱复印后,漫漶(音‘患’)残缺,均用墨補,而背面透过之墨痕,则用粉填,工作单调而繁重。老妻在编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的百忙中还助我操作,一灯对坐,直至深夜,亦不可不记。
一九九二年五月 畅安王世襄